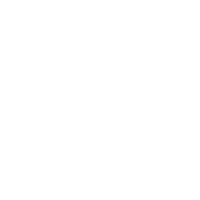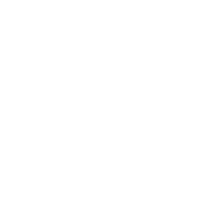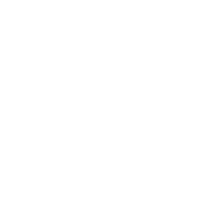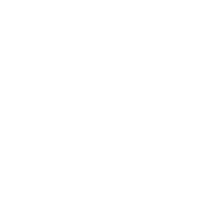自1986年至今,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留学生教育蓬勃发展,已累计培育了两万余名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,有力促进了多元文化交融互通,构建起了开放包容、充满活力的国际学生培养格局,有力推动了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的提升。特别是自学校第五次党代会以来,学校大力推进开放办学体制机制改革,实施国内外合作交流质量提升“丝路工程”,构建高水平开放办学新格局。即日起,党委宣传部(新闻中心)联合国际学院推出“我与首经贸留学生的故事”专题报道,生动展现首经贸教师与留学生之间的动人故事,擦亮“留学中国”北京品牌,期待为读者呈现一幅丰富多彩、充满活力的留学生培养画卷。
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国际学院刘一杉老师的文章,感受他与留学生之间的生动故事。
留学生是一扇窗
“你们在晚上洗澡吗?”
“中国人吃竹子吗?”
“每年春节的时间为什么都不一样?”
“立交桥下面为什么有许多跳舞的人?”
……
从2008年作为教学实习的研究生走上讲台,为留学生讲授汉语类课程,到今年(2024年)已经17个年头了。这些年来与留学生相处的经历越来越让我觉得:留学生就像一扇窗,让我看见世界,照见自己;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汉语、汉字,读懂了中华文明。
透过学生,我看见世界
“不同国家的人洗澡的时间安排不同”,这是我在教学生涯中发现的第一个文化差异点。在带学生练习 “什么时候”这个短语的环节,我最初只是随机地设计了一些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——比如“什么时候吃晚饭”“什么时候洗澡”等等——也没期待有什么特别的效果。但学生们的回答让我意外,我的回答让他们比我还要意外。许多学生说他们习惯早上起床后洗澡。我说中国人一般晚上睡前洗澡。他们听到后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,觉得难以理解。我解释说,对于许多国家的人而言,洗澡是为了良好的公众形象。对中国人来说,洗澡是为了缓解疲劳以及创造一个清洁的睡眠环境。
几年前的一个冬天,一个蒙古女孩在课间问我:“中国人吃竹子吗?”我心里暗笑:“中国人虽然爱熊猫,但也不至于跟熊猫一样吃竹子呀!”我回答:“不吃。竹子小时候(‘笋’字她还没学,我只能这样解释)可以吃,长大了就不能吃了。”她非常肯定地说:“不不不,我看见卖水果的地方有卖竹子的,很多人买。”我突然懂了:“你说的是不是‘紫色的竹子’?那叫‘甘蔗’。”
一个个类似这样的问题让我意识到:蒙古国没有甘蔗,柬埔寨没有电梯,很多西方国家没有枣。人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,经历不相同,因此我们各自的日常可能就是对方的新世界。留学生就像一扇窗,让我在小小的教室里,领略世界的多彩。
从那以后,“你什么时候洗澡?”“你喜欢吃什么食物”就成了我课上故意安排的问题。问题虽小,却能激发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。如今,不论什么样的回答都不会再令我意外,但是学生们发现彼此的文化差异时,却还是能瞬间兴奋起来。学汉语的机缘,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。
学生的问题,推动我认识中国
“春节的时间为什么每年都不一样?”可能是这些年来我遇到的留学生提出的最让我为难的问题。
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,我自己也不懂,根本无法回答。于是课后,我认真地查阅学习,之后发现,对这个问题的解释,几乎连接着整个农历系统的所有环节,包括纯阴历年和回归年的时差、节气与阴历月的关系、闰月设置的条件和要求等等。终于,我自己搞明白了,便又开始发愁如何给那些刚学了“你好”“谢谢”“再见”的留学生解释如此复杂的问题。
后来的实践证明,这个问题不可能简单地解释清楚。但我自己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也收获了许多。我不禁深深地赞叹先人的智慧。在没有钟表,只能“夜观天象”的时代里,农历作为一种混合历,既具备纯阴历简便易行的特点,又兼顾纯阳历指导农时的功能,这种设计需要多么长时间的观察积累,多么精妙的推衍和计算啊!
当然,教学中遇到的更多问题还是关于我们的生活细节的。比如:“为什么街上有那么多早点摊儿?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在家吃早饭,而在街上吃?”对于其他国家,尤其是许多西方国家的人来说,从容而正式的早餐是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要且有仪式感的环节。相较于我们的鸡蛋灌饼、油条豆浆,在他们看来可能过于“简单”了。如何回答这个问题?在那一瞬间,我想了许多:街头茶点的传统,人们对饮食的要求,超大城市通勤的时间,生活的压力,甚至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。所有这些原因可能都在街头早餐中有所反映。煎饼油条虽小,却折射着这个大国的方方面面。
再比如,“菜”字可以指蔬菜,也可以指一盘盘做好的菜。在讲第二个意思的时候,我通常会展示一张照片,上面有一份米饭和两个家常菜。我问留学生“有几个菜?”学生几乎一定会说“三个菜”。我也是通过这个问题才认识到:似乎只有中国人会严格地区分“主食”和“副食”。我们的米饭、面条不是菜,豆包、烙饼也不是菜,连“大丰收”也不能算是菜。作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,“粮食”这个概念,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地位。这一点,外国学生很难马上接受;而我,也是在外国学生的困惑中才更深刻意识到文化的差异。
在课上给学生播放的电视剧片段里,学生看到了长辈给晚辈布菜,觉得不太理解;“你多大”可以问平辈或晚辈,但不能问长辈,学生觉得“有点麻烦”;更不用说我们著名的“亲属称谓系统”。中国的家庭观念、长幼秩序,都渗透在生活语言里。这些习惯于我本是“默认设置”,就像是鱼身边的水。因为留学生的反馈让它们在我头脑里清晰了起来,仿佛鱼跃入空中,才知道自己原来在水里。

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本科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本科